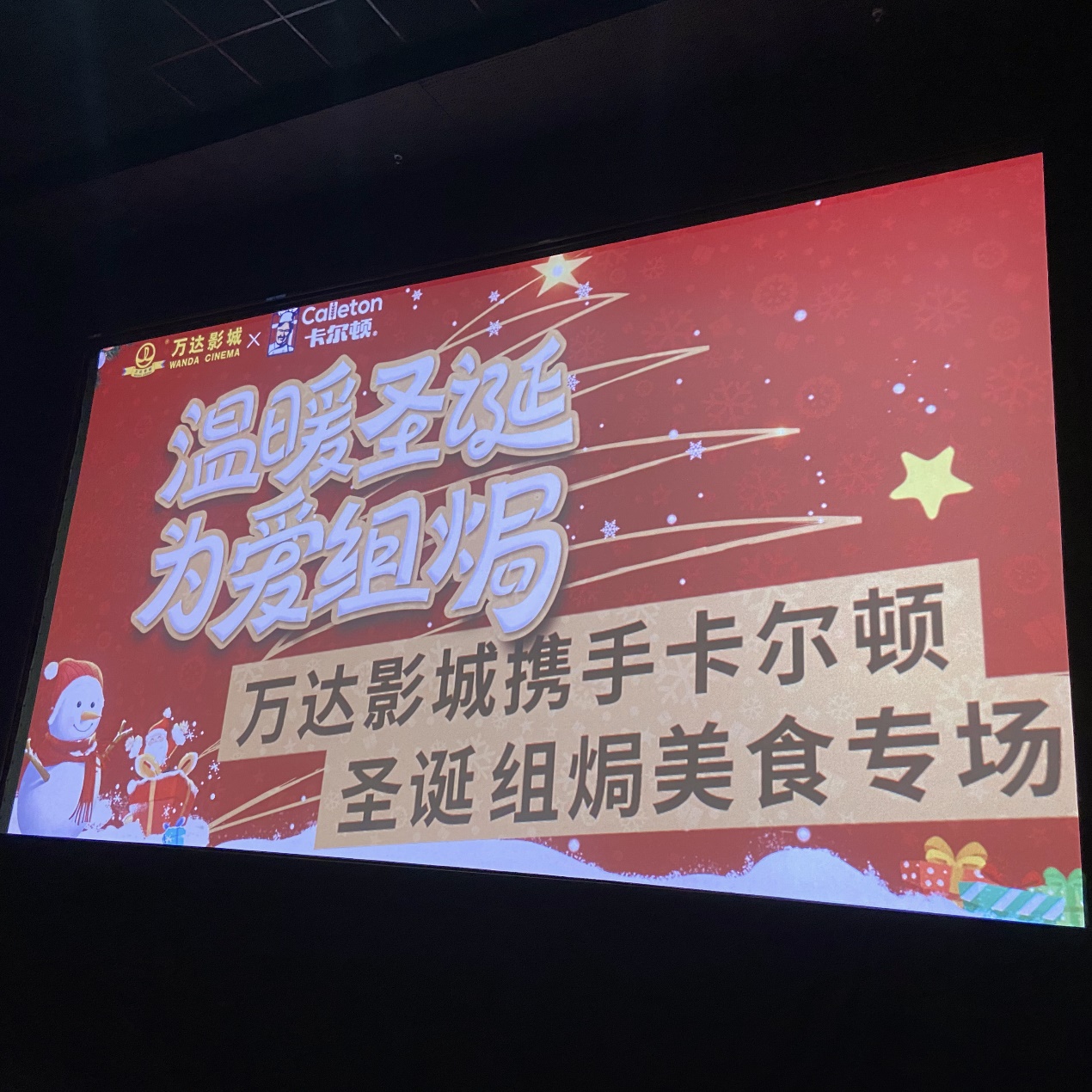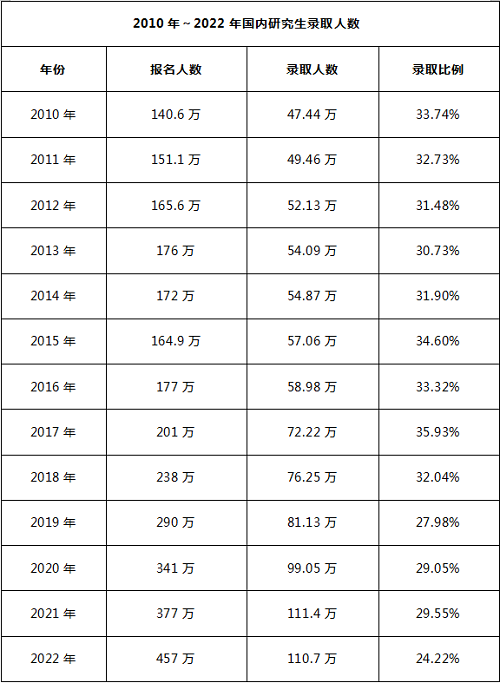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一直是全国风湿免疫学界的领头羊,蒋明作为其中一员,在国内开展风湿病相关实验室检查方法研究,较早建立了17种抗核抗体的检测方法;主持完成“抗核抗体谱的建立及临床应用研究”“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与基础研究”等多个项目;主编的《风湿病学》专著于1996年获中国图书奖、1997年获国家图书奖。从医几十年来,她熟悉掌握免疫性疾病及风湿病的基础理论、实验室检测技术,是一位具有丰富临床诊断与治疗经验的风湿病学专家。
【听医者讲述】
采访完成于蒋明教授九十岁高龄之际。在交谈过程中,我屡屡钦佩于她的神采飞扬、精神矍铄。我能看到,她炯炯的目光里满载着对医学事业的热爱、对生活的激情;我能想象,年轻时的她是如何怀揣着一腔热忱去开创学科、攻克难题、编写著作的。她说,人活着只为一件事:快快乐乐地为世界做贡献。这样开阔的心胸与境界,值得我们所有年轻人学习。
1957年,我毕业后留在协和做住院医师。住院大夫要写病程志,包括描述症状等,比如“今天病人吃饭不好,肚子有点疼,有点拉稀”这样就可以。但是,对病人这样的表现,自己得去思考为什么,患者的病到底是什么。有时我觉得某个病可能和哪方面有关系,我就去图书馆查书,或者跟别的同事一块儿讨论。等有一些思考了,我赶快把这些思考写在病程志里。上级大夫一看,说“你是动了脑筋了”。
我记得有一个女病人肚子胀水特别严重,我们第一反应是有肝硬化,因为那会儿肝硬化的病人挺多的。结果实习大夫放水后发现肚子里有一块疙瘩,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再仔细检查,发现是一个卵巢囊肿。我们请妇科大夫把卵巢囊肿切了,病人就好了。像这种病例,在我做了六七年大夫以后就看得多了,思维也广了。
协和有一套很好的制度。比如大查房制度,往往需要住院大夫介绍病例。其实做一个病例报告是不容易的,时间大概只有五到十分钟。怎么把病例介绍完整,让人听清楚,从而激发大家的讨论,是很考验人的。我就得想办法完成这项任务,从中学到很多。
我做总住院医师是在1963年左右。在这一段时间里,我接触的病人特别多。那时候拿出我写的病历,大家都说好。我一有空就往图书馆钻,看看有什么可参考借鉴的东西,或者借书回来半夜看,两个眼圈常常都是黑的,跟熊猫似的。
改革开放后,国家派访问学者去国外学习,我有幸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(UCLA)学习了两年,1980年去,1982年回来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的心情就像刚到协和上解剖课时一样,很激动。那时候国内的加样器是一个橡皮球,一捏,液体就随着玻璃管上来了,要多少挤多少。而在国外,定好用量以后,机器一按就出来了。我看着就想,我们怎么没有啊!
我当时想,国家并不富裕,却愿意花那么多钱来培养人才,把我送出国待两年,我一定不能辜负国家的希望,我一定得干出点事来,否则对不起国家,对不起人民。
我在UCLA主要学习抗核抗体谱的内容,学了很多抗核抗体提取、制作方面的知识,这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。某一些风湿病有特殊的抗体,你如果在患者身上测到某种特殊抗体,就可以诊断他患哪种病,所以这种特殊抗体又被称作“金标准”。比如红斑狼疮患者有一种特异性抗体,抗Sm抗体,这是华裔教授陈永铭在一名去世的红斑狼疮患者血液里发现的。如果在别的患者身上也测到这个抗体,那么几乎就可以明确诊断了。
当时,这类“金标准”在全世界很少有,美国的医院里也很少见,不容易要过来。但我很幸运,在我离开的时候,陈永铭请实验室将他们有的“金标准”全都给我了。他说,这个东西与免疫学相辅相成,中国这么大,咱们应当有,有了它,可以让免疫学飞速发展。
回协和以后,我在风湿免疫科工作,那时已经建科了。那会儿实验室的同事能提取抗原,但提取抗原后还要找到抗体,他们面临一些困难。我毫不犹豫地把所有“金标准”都拿出来,交给了主任。有了这些“金标准”,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很确定地诊断红斑狼疮、干燥综合征、硬皮病等疾病了。我心里高兴极了,觉得自己那两年没白去。
建科初期,有很多困难,但我觉得从事科学工作的人,不要想别的,要一心把工作做好。我那时身体很壮实,为了开展实验室的工作跑了好多单位,向他们寻求帮助,很多实验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的。我记得有时已经挺晚了,我还坐公交去看我养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关节积液里的细胞,来回来去地跑,也不知道累。
我有不少以耳鼻喉症状表现为主的病人,耳朵不好或鼻子不好,检查出来却是类风湿或者红斑狼疮。我记得有一个病人眼睛失明了,眼底都是絮状的,什么都看不见,眼科看完说是免疫病。我接手后,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,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。我没有治好他的眼睛,但救了他的命,让他活了下来。慢慢地,我看了很多病人。结合这些病例,我认识到,看病不能死盯着书上说的,要灵活地来思考。
后来,理论、经验等各个方面都比较成熟了,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主张,于是决定写一本全面的书。我搜罗了许多与风湿病相关的内容,看有哪些专家学者在这些方面是擅长的,我去找他们。比如病理学专家,有资深的经历但没有钻研过风湿病的病理材料,我就拜托人家在这方面学习总结一下。我尽可能地找了对风湿病比较了解的各个科室,在他们的帮助下编写了《风湿病学》,包括了风湿病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。
回顾这么多年的从医生涯,我真的很喜欢我的病人,有些病人我真是太爱他们了。虽然救治过程中我花了一些力气,但是看到他们能够转危为安,我心情挺愉快。有一个肝脏功能明显损害的自身免疫病患者,来医院的时候人都快不行了,我坦白地告诉他,病情太重了。他说:“你死马当活马医,帮我治吧。”我就拼命地治这个病人,早晨早点起来看他,晚上下班又去看看他,给他处理一下。结果这病人就好起来了,现在还带孙子了。他每年都来看我,我们变成了挺好的朋友,他知道我喜欢吃柿子,每年都给我带点柿子来,他前两天刚来看过我。
我觉得跟病人交朋友是很重要的。得让病人信任大夫,跟大夫交朋友,这样病人才会有什么事都跟大夫说。现在还有不少病人朋友常常来看我。我想这是因为我努力了,跟病人交心了。(本报记者崔兴毅整理)